撰文 | 倪瑜遥
编辑 | 黄月
在近期院线电影中,《姥姥的外孙》可算一匹黑马。影片上映一周已跻身中国市场泰影票房历史前三,截至目前的豆瓣评分为9.0。
电影以清明祭祖仪式开始,以姥姥的葬礼结束,一个散居在泰国暹罗的潮汕家族是其中主角。子女成年后搬离父母家,三代人的生活渐行渐远:守着老屋的姥姥信观音菩萨,坚持不吃牛肉;大儿子阿强炒股,小儿子索伊赌博,女儿阿秀在超市当店员,各自奔忙;外孙阿安已不识得潮州话,辍学在家,幻想成为游戏主播。

影片的主题是照护和亲情,其叙事延续了华人家庭片的含蓄温情。但导演并未止步于情感层面,而是直指亲人之间的利益纠葛。温情之下是坚硬的内核:期许获得遗产可以构成照护亲人的动机吗?当维系孝道伦理的土壤瓦解,还能靠什么来支撑家庭照护的责任?
家庭情感与利益战争
在清明祭祖仪式上,姥姥意外摔倒,之后被查出患癌。外孙阿安自此开始对姥姥的照护。他回到潮湿的老屋,被拉回到姥姥的生活节奏中。每天五点起床卖粥,给门前的花木剪枝浇水,按时带姥姥去医院化疗。同时也受到姥姥的管束和挑剔:冲茶拜神的水不能用微波炉加热,观音像不能移动,睡觉只能在楼下。

近年来,家庭照护作为情感劳动、亲情羁绊的主题常被书写。对于照护者而言,照护亲人是时间、体力和精神层面的多重付出,也是在陪伴中重新理解亲人、认识死亡与告别的过程。界面文化此前曾专访《照护》一书的作者凯博文,他指出:“人性的‘在场’(presence)是护理和照护中必不可少的元素。”
当下的照护书写多侧重于情感经验,或多或少回避了对于利益的探讨。《姥姥的外孙》更进一步,剖开亲人之间的利益冲突,试图补全在情感之外更立体的照护图景。
除了是病人,姥姥还是有遗产待分割的家族长辈;除了是照护者,阿安还是需要本钱立足的年轻人。无论是阿安、母亲还是两个舅舅,他们都惦记姥姥的遗产;而姥姥对财产分配也自有打算。这些纠葛并未随疾病而隐退,在绵密的亲情下,一场家庭战争如火如荼。

照护换遗产?
阿安照顾姥姥的初衷很功利——他想要姥姥的房子,他需要一笔钱。看到表妹阿梅照顾姥爷并最终继承房产,他决定依葫芦画瓢,把姥姥当作“本钱”。尽管阿安也怀疑过这是否妥当,但自始至终,他对利益的诉求并未改变。
事实上,影片中的人物并不避讳谈论钱。金钱的力量在大儿子阿强身上体现得最明显。姥姥摔倒后,阿强没时间照顾姥姥,给了妹妹阿秀一笔“陪护费”。此后他还想给阿安“工钱”,作为照顾姥姥的酬劳。阿秀让阿安多陪陪患癌症的姥姥,阿安的第一反应是“你给我发工资吗?”在情感之外,金钱也是连接家族成员的纽带。
就连姥姥也抱怨:她任劳任怨地照顾父母,但父母什么都没留给她。她的怨言反映出一种观念:家庭照护作为一种情绪劳动,很多时候由女性承担,却常被认为是琐碎且无偿的,至少在劳动过程中是无偿的。
英国作家罗斯·哈克曼在《情绪价值》一书中指出,与体力劳动、智力劳动一样,情绪劳动也是一种需要时间、精力和技能的工作形式。在性别权力结构中,情绪劳动被认为是女性化的,但人们却常常忽视这种劳动的真正价值,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内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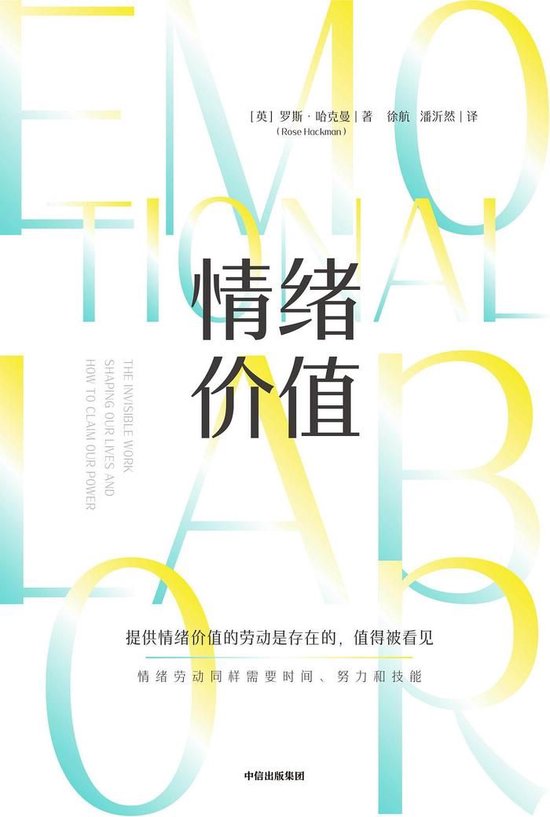
《情绪价值》
[英]罗斯·哈克曼 著 徐航 潘沂然 译
中信出版集团 2024-02
在华人的传统观念中,家庭照护是孝道伦理的一部分,子女照顾老人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。在当代社会,这种“天经地义”却可能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。今年4月,胡泳在《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》一文中谈到:“在照护老人这种事情上,也需要开家庭会。怎么分工,去不去养老院,得病了怎么治疗。中国人有个特点,很多事儿不明说,说了好像伤和气。恰恰是很多时候你不明说,暗流的涌动就会导致很多矛盾。”
父权制本位的孝道伦理压制了对于照护者的责任与利益的探讨。孝道以家长的支配性权威为前提,照护者与被照护者之间并非平等关系。孔子主张“事父母几谏,见志不从,又敬不违,劳而不怨”,晚辈对长辈的供养义务被强调,而对利益分配的诉求则可能被视为不敬。
在华人传统社会,即便女性承担了照护责任,在财产分配中也难有话语权。法学学者罗冠男指出,在中国传统的继承制度中,财产被严格地留在父系家族内部,以保证家族的延续。女性难以像她们的兄弟和丈夫那样继承财产。
这一不平等的原则在影片中也有所体现。尽管姥姥承担了照护父母的主要责任,但她没有继承遗产,因为家人认为“即便财产分给她,也会被她败家的老公花光”。到了下一代人,相比于阿强和索伊,女儿阿秀付出了更多精力来照顾母亲,但母亲同样没有把遗产留给她。

对于更年轻的阿安和阿梅来说,他们照顾长辈的主要动因并不在于孝道伦理的约束,而在于与其他亲属竞争遗产。尽管有人批评“为了遗产而尽孝”的价值观,但这恰恰是影片的一大亮点。电影直指照护者的责任与权利这一常被遮蔽的问题。当维系孝道伦理的家族和礼法土壤瓦解,期许应得的利益回报也是照护者的正常心态。
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葛玫在著作《谁住进了养老院》中谈到,人口流动、个体化、生育率下降等因素使子女越来越难尽赡养老人的儒家孝道。老年父母选择住进养老院,或者减少自己的需求,但他们并不愿意用“不孝”来评价子女。社会学者吴心越在其关于养老机构的论文中也指出,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加剧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,更多子女将老年照护“外包”给养老机构。养老机构作为“孝亲代理”重新嵌入家庭秩序和孝道文化,建构起照护专业主义。
拆解空洞的“孝”
无论是父母主动住进养老院,还是子女将孝道“外包”,都反映出了一个问题:当传统孝道在现代社会衰落,我们需要新的话语资源来理解照护和养老。《姥姥的外孙》中的台词“多出力者应该多得遗产”就是一种对于照护的阐释。阿梅则是这一观念的成功践行者。
电影中有一个细节:包括姥爷在内的亲属都觉得阿梅应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,而不该守在姥爷床头。言下之意,照护失能老人是尽孝,但牺牲了自己的前程,并不划算。在这套价值体系中,为家族付出的孝道伦理让位于功利的个人主义。
学习护理专业的阿梅看待照护的视角则更加“职业化”。她尽职照顾瘫痪的姥爷,在姥爷心目中爬到第一位,最终在姥爷去世后继承房产。于她而言,照护亲人是一份“轻松又赚钱的工作”,发挥专业技能,付出时间、劳动和情感,换取利益,毫不拖泥带水。一端是照护的责任,另一端是优先继承遗产的权利,这是阿梅重新给出的天平,直接而自洽。
但如果说阿梅和阿安对于长辈只有功利的算计,也不尽然。阿梅很干脆地卖掉姥爷的房子,但当阿安问她是否梦到过姥爷,她含泪说姥爷一定去了极乐世界,不会再牵挂她。她的祈愿也发自内心。在得知姥姥将房子给了舅舅索伊时,阿安生气地指责姥姥爱错了人。但姥姥去世后,他将姥姥为他存的钱全部用来买墓地,这份付出也心甘情愿。
影片中还有一段精辟的对白,阿秀对母亲说:“儿子继承遗产,女儿继承癌症。”母亲回应她:“我不知道最爱谁,但最希望你在我身边。”女儿压抑多年的委屈是真实的,母亲在生命尽头的依恋也是真实的。
照护病人的辛劳和对现实利益的渴求,感性的挂念与理性的计算,疾患降临在姥姥身上,也将这个潮汕家族推向纷乱的潮水中。当主人公们从父母之仁和子女之孝的框架中松绑,亲人之间自然流淌的是更复杂也更真挚的感情。解构空洞的孝道,转而描摹家庭内部现实而幽微的羁绊,这或许也是《姥姥的外孙》动人的地方。














